

一、研究背景
家庭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组织,在推助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方面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而目前几乎所有研究和谐社会的课题和专著都未将和谐家庭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框架中的一部分,从唯一的通俗读物《和谐家庭建设读本》看,由于缺乏学术背景和实证研究基础,只是简述了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基本内容,未对和谐家庭的概念、特征和评估指标等进行探讨。随着离婚率的持续上升以及大众传媒对所谓的“闪婚”、“闪离”、婚外恋、“包二奶”、情杀等典型案例和隐私故事的过度渲染,加上各种存在严重样本偏差的所谓随机调查(实为方便抽样、随意调查)统计结果的广泛复制和传播,以致许多公众对当前中国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自由泛滥以及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深表忧虑。于是,一提起和谐家庭建设,就把它归结为家庭美德教育和伦理建设。以国家社科基金发布的课题指南为例,多年来社会学学科与家庭婚姻有关的选题招标几近于无,人口学领域主要集中在与计划生育后果和政策有关的项目,而历史学学科2006年和2007年连续发布“中国近代家庭结构变动与‘孝’的观念的发展变化”选题指南,哲学学科中的“家庭美德建设研究”从2003-2008年已持续六年以同一选题出现在招标指南中;上海市社科规划基金社会学学科多年来唯一与家庭有关的项目指南为“和谐社会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研究”。
然而,把道德作为和谐家庭的唯一评价标准,显然忽视了家庭需求和关系质量的多元化和多层面。其实,向家庭成员进行道德灌输,强化其义务感、责任心,只是和谐家庭建设的目标之一而不是其全部。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试婚同居、青少年避孕、虚拟婚恋、契约婚、无性繁育等新伦理问题日渐凸显;而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使经济和工作压力成为家庭的普遍焦虑;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生存时代儿童社会化、教育功能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子代沟和冲突,速变时代的价值观念、志趣爱好、个体目标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及多变性,使家庭中亲密关系的调适、子女教养、老人照顾和家庭危机的有效应对等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和谐家庭新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特征如何在扬弃传统家庭规范的同时注入现代新价值、新取向,以及家庭伦理教化的内容和有效方式等都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和积极倡导。此外,家庭如何通过发掘内外资源、提升成员间的凝聚力和社会适应力,发挥家庭的正功能,以回应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也是快速变化的风险和竞争社会提出的新课题。
本研究的必要性还在于和谐家庭指标体系专题研究的极其匮乏。经搜索数字电子期刊网发现,不仅和谐家庭的专题研究极少,研究和谐家庭指标的相关文献只有一篇,而且不仅评价指标存在重大缺陷,同时也未对和谐家庭的影响因素加以探讨。因此,本课题的设立将有助于填补和谐家庭研究的缺位,并对既有指标体系的缺陷加以修正,同时,通过分析家庭和谐的影响机制,对改善家庭生态环境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服务提出积极建议,以使进一步提升婚姻质量和家庭凝聚力,增进家庭成员的福利和幸福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二、文献回顾和评述
(一)国内相关测量及其评述
和谐家庭的指标研究仅有一篇相关文献,即《关于家庭和谐状况的评价体系研究》,与家庭精神文明测评体系的研究探讨的都是家庭生活和关系质量。但因这些测评指标尚在试行中而未予公开发布,我们仅获得其中“全国文明家庭评价指标体系”和“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十一五’测评指标”的文本(内部印刷版)。因此,本文对国内和谐家庭或文明家庭测量指标所作的评述,均以这三个范本为参照。笔者认为,上述指标体系无论是总体框架还是具体的测量指标都存在重大缺陷。
1.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的混淆
在《关于家庭和谐状况的评价体系研究》中,夫妻感情不深、夫妻价值观不同、夫妻性格各异、家庭伦理道德缺失、家庭传统观念严重、亲子教育方法不当和婚姻家庭中的方法与技巧缺失7个因素是导致家庭不和谐的主要成因,并以此7个层面构成家庭和谐状况评价指标体系。且不说作者一方面将这7个侧面都视作家庭不和谐的成因,一方面又把它们都作为评价体系中的7个层面,本身就混淆了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也不说夫妻价值观不同、性格各异是否与家庭和谐直接相关;仅以“夫妻感情”侧面的具体评价指标看,“婚姻自主率”、“恋爱时间长度(谈恋爱时间最好不要短于6个月)”这两项变量,也并非是度量夫妻感情的有效指标,甚至未必是夫妻感情的决定因素。比如,一些父母包办的老年夫妇,尽管没有6个月以上的浪漫恋爱经历,但几十年来却和谐相处、相濡以沫,而不少青梅竹马、婚前感情笃厚的夫妻,婚后却难以协调适应甚至劳燕分飞。家庭文明测评体系中的一些指标,如“家庭藏书量≥300本”、“住所布局合理,简洁明快,舒适宜人,干净整洁”、“对子女状况的满意度≥80%”等,或许只是家庭和谐的影响因素(甚至连影响因素都不是),并非是家庭和谐的评价指标。
2.评价领域及评价主体的公私混淆
对家庭是否文明、和谐的评估应聚焦于家庭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质量,而诸如“见义勇为,弘扬正气”、“对老、弱、病、残、孕者主动礼让”、“人文知识知晓度≥60%”、“对科学观念和方法的认可度≥70%”、“工作努力,勤劳致富”、“奉公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等项目,多为社会公德评价指标而并非测量家庭和谐的直接指标。此外,文明家庭测评的不少指标如“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夫妻感情融洽”、“消费合理,开支适度”、“无家庭矛盾和家庭暴力现象”、“住所布局合理,简洁明快,舒适宜人,干净整洁”等,均需由“居/村委会评议、妇联核定”,而随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日渐分离、个人隐私权观念日渐为社会所公认,居/村民的夫妻感情、亲子关系、家庭矛盾、消费理财及个人习惯等家庭隐私通常不为外人所知。况且,对情感和家庭生活质量是否满意很难有统一的公共尺度,不同的家庭对“感情融洽”、“开支适度”、“居所舒适”的期待各不相同,让社区、妇联来“核定”居/村民的家庭私密关系和生活质量,显然也存在评价主体混淆的问题。
3.量化指标重形式轻内涵
出于测评需要,一些学者和有关部门常设法以数字化指标来考察家庭成员的文明程度和相互关系,如“每天读书看报等学习1小时以上”、“每周参加体育锻炼2次以上(每次半小时以上)”、“常回家探望父母,每月1-2次”、“邻里相识度≥60%”、“家庭权力共享度≥75%”、“妻子决定家庭重大事项人数占丈夫人数百分比”、“家长每年参与4次以上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家庭成员有1项以上艺术爱好另加3分”等。然而,邻里相识度更多地取决于房屋结构(如封闭式公寓住宅的邻里间相识较少)、居住时间的长短、工作性质及个人性格;退休老年人通常有更多时间参加体育锻炼;那些泛泛而谈、质量平平的形式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即使参加次数再多也未必有成效;而一些家庭即便实权由一方握有也未必不和谐。此外,因工作需要或路途遥远,每年只探望父母1-2次甚至常年未探望也未必影响家庭关系。可见这些重形式轻内涵的量化项目并非是度量家庭和谐的直接指标。
4.对非标准和贫困家庭的歧视
以往的指标评估体系通常按中青年三口之家或三代同堂家庭的标准设计,于是,“每天与孩子一起活动、游戏”、“妻子月收入占丈夫百分比”、“丈夫家务劳动用时占妻子百分比”、“姻亲关系融洽度”,“教育投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20%/年”、“生活宽裕,家庭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书报、网络信息等学习投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3%以上”、“家庭电脑拥有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良好”、“室内及庭院绿化美观”等成为达标要求。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和模式是多元的,一些无子女或中老年家庭不可能“每天和孩子一起活动、游戏”,也无须参加家庭教育指导,有的单亲家庭没有丈夫或妻子、没有姻亲关系,许多项目无法回答;而那些贫困的或老年空巢家庭没有藏书、报刊和电脑,一些家庭成员身患重病、收入下降、生活拮据,或居处狭窄谈不上舒适宜人或绿化美观,难道这些家庭就缺乏温馨、难以和谐?
5.指标概念缺乏可操作性
由被访者自测的指标概念内涵和外延尤须明确,但上述评估体系中的许多变量,如“学习意识强,学习氛围浓,学习效果好”、“妻子自我提高用时占丈夫百分比”、“精神生活追求度”、“知晓常见病或慢性病的防治方法”、“科学理财,理性消费”、“学法、用法、守法,有防黄、毒、艾、赌、骗的知识”,“对婚姻、科学育儿知识认知度≥70%”、“家庭安全、节约环保知识知晓度≥70%”等根本无法操作。比如“学习意识”、“学习氛围”、“学习效果”、“自我提高”如何理解或操作?精神生活追求到什么“度”才最佳?另外,有的指标甚至需要另附一套操作化的细目,如常见病或慢性病有哪些,每种病的防治方法如何?况且有些“知识”是否有标准答案也难说,比如怎样消费才是理性、如何理财才是科学的?
由于指标缺乏可操作性,上述的和谐家庭指标和文明家庭指标体系似未经实证资料的检验,即未在和谐家庭和文明家庭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加以验证或推广使用。
(二)国外相关理论、测量及其评述
国外与和谐家庭评价的相关理论框架,较为通用的指标体系研究有家庭凝聚力视角、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以及家庭环境量表。
1.家庭凝聚力测量
“家庭凝聚力”是美国家庭学者在反思了物质至上主义、消费文化和极端个人主义对家庭的消极影响后提出的研究新视角。德弗雷等指出,美国20世纪的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家庭为什么失败”的问题上,21世纪的研究将更关注“家庭如何才能成功”的问题。家庭凝聚力研究视角并不否认家庭问题的存在,但它采用积极、乐观的世界观和生活取向,寻求“家庭如何创造性地和有效地迎接挑战”的途径。尽管媒体每天都在灌输着大量关于私通幽会、夫妻冲突、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负面故事,但对全球27个国家21,000多位家庭成员的调查结果显示,世界上大多数家庭有着相当的凝聚力,稳定牢固的家庭要比麻烦重重的家庭多得多。而家庭凝聚力模型可以激发和引导人们建立更令人满意的关系。其代表性测量主要是Stinnett等提出的家庭凝聚力量表,包括6个侧面:承担义务、尊重和情感、积极的交流、共度欢乐时光、精神健康和有效地处理压力和危机,多次修改后现有80多个项目。
2.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家庭科学系教授Olson等于1982年编制,共有30个项目,以5级评分。“家庭亲密度”侧面分为松散、独立、亲密、粘连4种类型。家庭适应性”侧面包括有序、无序、灵活、刻板4种类型。该“环状模型”中的“平衡型家庭”既具有较好的内部亲密度,又具有应对各种危机和压力的适应力。由费立鹏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的修订版,被国内医学和心理学界广泛引用于对精神病患者、酒精依赖者家庭与对照组家庭,以及大中学生家庭进行比较测试。实际上该量表已几经修正,现改为6种类型42个项目,而国内学界仍在沿用1982年的版本。然而,无论哪个版本,无论是家庭凝聚力量表、亲密度和适应性测量,都更适用于西方文化和家庭结构。比如,美国三代同堂家庭很少,他们对个人自由、独处的期待较高,宗教信仰的指标也较为重要,加上美国人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对题意的理解力也更强。因此,其中的“我们将困难和挑战看作是成长的机遇”、“家人之间能坦诚地分享各自的感受”、“理解做成一件事需要时间,所以互相给予对方充分的余地”、“我们家很好地处理了共处和独处的关系”、“家人之间可以随意谈论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家人对其他家庭成员朋友的事情知之甚少”等项目,或许未必适用于我国,此外,有些指标的题意、界限表述不够明确,或者口语化缺乏。如全盘照搬的话,国内农村的或低教育层次的调查对象在理解上会有障碍,由此影响效度。
3.家庭环境量表
被最广泛采用的家庭环境量表(FES)由美国心理学家Moss等于1981年编制,1991年费立鹏等在此基础上修订后成为该量表的中国版。该量表共有10个分量表90个是非题,分别评价不同家庭的社会和环境特征:1)亲密度;2)情感表达;3)家庭冲突;4)独立意识;5)成就意识;6)知识性;7)娱乐活动;8)道德观;9)家庭规则;10)控制管理。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重测信度,但成功性、娱乐性和控制性、情感表达、独立性、道德观等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差。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是跨文化影响对题意理解差异所致。但我们认为该量表的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混淆了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和家庭关系评价指标的区别。从指标的分类特征看,亲密度、情感表达、家庭冲突、独立意识等为家庭关系质量指标,而道德宗教观、成就意识、娱乐活动等显然不是家庭关系的评价指标,甚至只是间接的影响因素,如“我们认为无论怎样,离婚是不道德的”、“我们认为行贿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现象”、“家庭成员都认为使生活水平提高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我们家每个人都对1-2项娱乐活动特别感兴趣”、“我们很少外出听讲座、看戏或去博物馆以及看展览”、“我们家经常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们很少讨论有关科技知识方面的问题”、“我们家的人对获得成就并不那么积极”,有些指标甚至难以判断对家庭关系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
关于解释家庭关系质量的主要有资源论、生命周期解说、符号互动论、家庭压力视角、文化规范分析和社会资本论等,因篇幅关系在此不一一复述。
三、研究框架、方法和资料来源
(一)和谐家庭指标体系及其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
鉴于既往的相关度量虽有借鉴意义,但又不完全适合国情或存在含义不清及缺乏可操作性等局限,我们将在对前人已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加以扬弃,并依托相关的解释理论建立和谐家庭关系质量评价的影响机制模型。其中吸取了美国学者中的部分指标,如家庭凝聚力测量中的“家庭成员很容易察觉对方的情绪”、“都很强调有问题通过讨论来解决”、“家人间公平地分担义务和责任”、“互相坚守承诺”、“相互宽容,不抱怨”、“很少互相贬低”、“表露我们的爱”、“尊重各自的处世方式” 、“一贯注重遇事的灵活应变能力”、“经常在一起开怀大笑”、“家庭成员喜欢在一起共享美好时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的“在家庭有难处的时候,家人都会尽最大的努力相互支持”、“家中每个人都参与做出重大的家庭决策”、“当家庭中出现矛盾时,家人彼此能谦让并取得妥协”、“家庭状况有变化时,家庭平常的生活规律和家规很容易有相应的变化”和家庭环境量表中的“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充分的关心” 、“家庭成员经常公开地表达相互间的感情”、“家中每个人都可以诉说自己的困难和烦恼”、“家庭成员之间极少发脾气”、“家庭成员之间经常互相责备和批评”、“家人间都很注意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加以本土化的改进和修订,使之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同时,还吸取了家庭心理学、家庭治疗研究的前人成果以及我们以往多项经验研究中的一些指标,来构建符合国情的和谐家庭指标体系框架。
鉴于先前研究的一些缺陷,本研究和谐家庭指标体系的主要特征在于:
(1)以人为本,定位家庭关系质量。摒弃那些每天读书看报几小时、每周参加体育锻炼几次、每月探望父母几次、每年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几次之类形式主义的量化指标。(2)可操作性,适用不同结构家庭。不使用精神生活追求度、科学理财、理性消费、自我提高用时、与孩子一起游戏、教育投入比例、家庭电脑拥有率、丈夫家务劳动用时占妻子百分比、室内及庭院绿化美观等难以测量或不适用无未成年子女或单亲、困难家庭的指标。(3)可持续发展,关注家庭内外和谐。为了反映家庭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关系,本研究增加了家庭与邻里、社区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测量指标。
为了提高指标的效度,在设计有关指标时我们尽量使之通俗易懂和口语化,并将其所表述的内涵统一为具有正面的导向意义(如把“家庭成员之间经常互相责备和批评”改为“家人之间很少相互挑剔或指责”),以利于实务工作的使用。
其中一级指标有家庭内聚力和家庭适应性,二级指标为:(1)家庭内聚力侧面包括承诺、关爱、沟通交流和表爱、分享;(2)家庭适应性侧面涵盖尊重、包容、调适能力、内外和谐,合计31个三级指标。影响机制主要采用上面提到的资源理论、生命历程学说、象征互动理论、家庭压力视角、文化规范论和家庭系统论(见图1)。
图1 和谐家庭评价体系及其影响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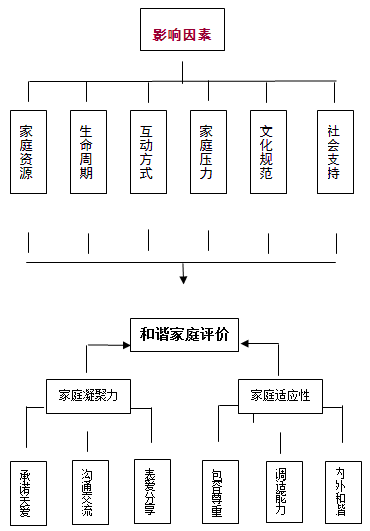
(二)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首先以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资料,对和谐家庭指标进行探索性测试,我们将采用因素分析方法,将31个三级指标复合成二级指标,也就是探索和谐家庭指标体系的具有内在聚合效度的潜在结构;其次,我们以新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各因子得分估计值的合成分数即家庭和谐度的总值,并以该总得分值为因变量,以家庭资源、生命周期、成员的互动模式、家庭压力、文化规范和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建立和谐家庭影响因素的解释模型。
本研究的资料来自对上海1200个家庭的调查,该调查按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从上海9个区/县22个街道/镇43个居/村委会中选取家庭,并以家庭中20-65岁成员的生日离7月1日最近者为访问对象,由经过培训的访问员入户进行问卷访谈。1200个被访者中男女各占50%,年龄在20-29岁的占13%,30-39岁的为24%,40-49岁的有28%,50-59岁的占27%,60-65岁的为9%。家庭人口在2-8人之间,户均3.57人,其中单亲家庭为2%,夫妻家庭有12%,核心家庭占45%,直系家庭有39%,其他家庭为2%。
(三)解释变量
1.家庭资源
(1)经济资源
由于不少被访者家庭有两个以上成年人(最多为6位),我们不可能询问到所有有薪成员的工资收入,而家庭财产也难以准确估计,且没有研究表明家庭财产对成员间的人际关系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只能使用被访者对自己家收入的主观估计来测量,即“和我国社会上一般家庭比较而言,您家的收入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该变量尽管难以反映家庭的经济资源,但其中所隐含的被访者心态(如知足常乐或攀比心理)或许会对家庭生活和关系的评估产生影响。
(2)精神资源:“家庭藏书量≥300本”曾被认为是和谐家庭的度量指标之一,实际上或许连影响变量都不是,我们权当藏书量蕴涵了和谐家庭的精神资源,把它纳入解释变量,但我们的假设恰恰相反:藏书量与家庭和谐程度无显著相关。
(3)社会支持:即在遇到急等用钱、孩子需要照看/辅导和烦恼苦闷/压力大需要倾诉/支持时得不到包括父母长辈、兄弟姐妹、子女、同事、朋友、同学、邻居、居村委会单位、市场和其他任何支持的3项相加之和。我们假设能及时获得社会支持与家庭和谐成正相关。
2.生命周期
在家庭各生命周期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压力和调适难度,而由于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我们仅以家中是否有7岁以下儿童或70岁以上老人为界作考察。
3.家庭压力
主要以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和其他家庭问题压力三个侧面来考察:
(1)经济压力:询问“在过去1年中,您家有没有面临下面所列的经济困难、限制或压力”,将其中“平时或到月底时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家庭日常开销”、“因日常开销/交学费/医疗费而向亲戚/朋友借过钱”、“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上技校或中专”、“有病不看医生/推迟看病/吃药/手术/吃低效药”和“因为家人下岗/失业/待业/经营亏本而降低了家庭生活水平”(0-2分别表示从没有到有严重)等5项相加;
(2)工作压力:将在过去1年中,被访者、配偶和其他家人是否面临经常出差/应酬/加班//换岗/定额过高/同事竞争等工作压力(0-2分别表示从没有到有严重)等3项相加。
(3)家庭问题压力:将在过去一年中,家中有无成员乱花钱、上网成瘾、“啃老”、酗酒、赌博、吸毒、犯罪或因婚外恋、嫖娼、卖淫等性问题引起的烦恼(0-2分别表示从无到严重)等8项相加。
4.互动方式
家庭成员效仿、制造、运用和改变语言、表情、声调、身体姿势等象征性符号的能力,对于家庭中的人际互动以及关系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使用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变量,即被访者回答的“在与家人(夫妻/父母子女)融洽相处方面的知识、技巧很欠缺”(1-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来估计。
5.文化规范
(1)由于夫妻关系已成家庭关系的轴心,婚姻观包括两个侧面:
一是对婚姻重要性和终身婚姻的认同,将是否认同“一个好的/幸福的婚姻对自己的人生非常重要”和“婚姻是神圣的,结了婚就要白头到老”(1-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两项相加,二是对美满婚姻的认同,将是否认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和“现在很少有美满、幸福的婚姻”(1-5分别表示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两项相加。
(2)孝亲观:
将“子女应尽自己的力量赡养父母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舒适”和“好好孝敬、侍奉公婆是媳妇应尽的责任”(1-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两项相加。
(3)邻里观:
以是否认同“听到邻居夫妻激烈争吵,只要与自己家无关就不必去劝阻”(1-5分别表示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来测试。
此外,我们把城乡作为控制变量也进入解释模型。
四、研究结果
(一)和谐家庭指标体系的潜在结构测试
为了验证和谐家庭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我们首先进行探索性的因素分析,即把31个指标中相关性较强的变量通过主成分法抽取共同因子归为一类,推导出和谐家庭指标体系可能包含的潜在类别,并以最优斜交转轴决定因素负荷量,删除概念归属跨类别且因素负荷值小于0.45的5个变量,其余26个变量组合成与原先假设类似的5个新类别,被分别命名为“承诺、关爱”、“调适能力”、“尊重、包容”、“表爱、分享”、“内外和谐”,特征值在3.7-7.5之间,总解释量为56.4%,KMO为.95。26个变量的Alpha系数为.92,各新因子的信度系数也在.65-.86之间,表明该组合量表所选用的指标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和良好的结构效度(见表1)。
表1 和谐家庭指标体系的因素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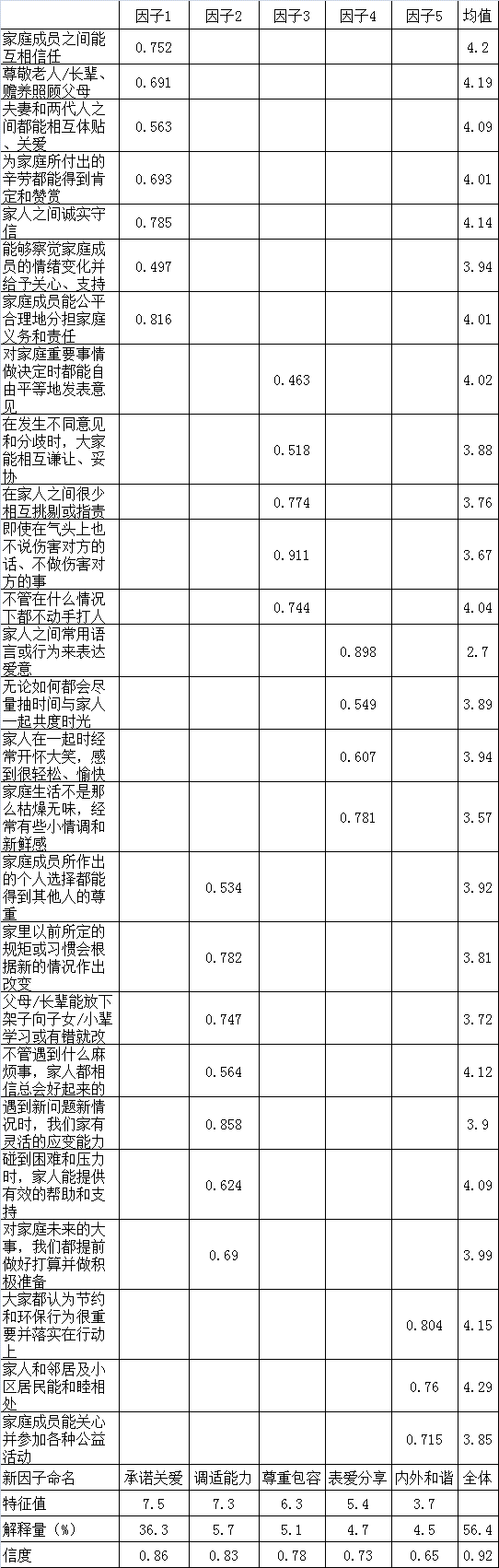
上述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了和谐家庭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即家庭凝聚力侧面包含“承诺、关爱”和“表爱、分享”两个分量表,家庭适应性包含“调适能力”、“尊重、包容”和“内外和谐”三个分量表,合计共26个指标。分析结果大致证实了我们原先预设的和谐家庭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未进入指标体系的5个变量都是原先被假设为“沟通交流”类别的指标,如 “在遇到问题或冲突时总是采取讨论、协商的方法来解决” 、“能耐心倾听家人诉说心事/听取不同意见”、“对于家人的缺点错误,我们都能体谅并给予纠错的机会”、“能经常看到家里人的优点、长处并赞扬他/她”、“家人之间都能尊重各自的个性与处世方式”。这些在西方学者看来很重要的指标之所以被剔除,未必表明这些沟通交流的方式在中国不重要,而是因为沟通交流贯穿于家庭成员间的互敬互爱、感情表达和协调适应之中。此外,个别沟通交流题项依然不够中国化或通俗化,或许也增加了被访者准确理解的难度,由此降低了指标的效度。
(二)家庭和谐度的基本状况描述
上海家庭的和谐程度究竟如何,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有什么特征?本研究将通过对26项和谐家庭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加以阐述。
1.上海家庭和谐指数的总体水平较高
我们以因素分析所提取的各新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5个因子得分的合成分数作为家庭和谐指数的总得分,同时将每个家庭的总得分换算成最低为0、最高为100分的数值,并将此值均分为5等分。结果表明,只有1%的家庭总分在20分以下,3%的家庭约在20-40分间,处于中间层次即40-60分的占到26%,在60-80分之间的比重最高,达53%,获得最高的即在80-100分的家庭约为17%。这个分布显示了上海家庭总体和谐度较高的基本概貌。
2.承诺、关爱指数高,表爱、分享尚不足
从和谐家庭指标的分类变量看,在家庭凝聚力侧面,家人间在互敬互爱、互信互助方面的得分较高,除了细微之处即“能够察觉家庭成员的情绪变化并给予关心、支持”尚有欠缺外,其他6项指标的平均得分都在4分以上(见表1)。其中被访者认为“家庭成员之间能互相信任”、“我们家在尊敬老人/长辈、赡养照顾父母方面做得很好”、“家人之间诚实守信”和“夫妻和两代人之间都能相互体贴、关爱”完全符合或比较符合目前家庭状况的均在九成上下。“承诺与关爱”侧面7项指标的均值、中位值都显著高于“表爱与分享”侧面(见表2)。后者4个单项指标的均值都在4分以下,尤其是“家人之间常用语言或行为来表达爱意”一项的均值仅为2.7分,在所有26项指标中为最低(见表1),回答该项非常符合或比较符合目前家庭状况的分别只占6%和19%,认同“家庭生活不是那么枯燥无味,经常有些小情调和新鲜感”非常符合目前家庭状况的仅占9%,这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家庭成员在情感表达和营造浪漫氛围方面仍存在欠缺之处,尤其在郊县。
表2 和谐家庭各侧面得分的描述性统计

在家庭适应性侧面,内外和谐的指数较高(均值为4.10分),其中尤以“家人和邻居及小区居民能和睦相处”方面的打分最高,认为完全符合的达33%,比较符合的占63%;“大家都认为节约水、电、煤和垃圾分类等环保行为很重要并落实在行动上”非常符合被访者家庭实际的占30%,比较符合的有59%;但在对“家庭成员能关心并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作判断时,持相同回答的分别只占18%和56%。
被访者的邻里观或许也可在一个侧面佐证家庭与周围邻居的和谐相处,在对“远亲不如近邻”作判断时,只有7%“的被访者对此持否定回答,对于“听到邻居夫妻激烈争吵,只要与自己家无关就不必去劝阻”的说法,持非常赞成和比较赞成态度的只占12%。
4.协调适应能力强,尊重、包容待改进
大多数家庭“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事,家人都相信总会好起来的”(达93%),在“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时有灵活的应变能力”(为82%),75%的家庭会“根据新情况对以前所定的规矩或习惯做出改变”,91%的家庭在“碰到困难和压力时,家人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支持”。这些都表明上海家庭在情况发生变化或面临困难、危机时,通常更多地以积极的态度做出有效的应对,具有协调适应的弹性和能力。
但统计结果也显示,尽管“在对家庭重要事情做决定时,大家都能自由平等地发表意见”的占到86%,但家庭成员人际互动中相互尊重和包容仍有欠缺,如“家人之间很少相互挑剔或指责”的比重相对较低,占72%,“即使在气头上也不说伤害对方的话、不做伤害对方的事”只占65%。
(三)家庭和谐指数的影响因素
为了估算不同变量对和谐家庭指标体系的净影响,我们分别以和谐家庭总分值和各维度的因子分值为因变量,建立综合回归模型和5个多维回归模型。在排除了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基本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符号互动论、家庭压力视角、文化规范分析和社会资本论的假设。其中综合模型的R2为25%,多维模型分别为22%、19%、15%、15%和13%(见表3)。
表3 家庭和谐指数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Beta值)

回归模型报告了如下分析结果:
(1)社会文化对和谐家庭的构建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美满幸福、白头偕老婚姻的高度信仰和期待、对敬老孝亲、邻里互助的认同率越高,家庭凝聚力和适应性指数显著较高(在文化规范的4个变量未纳入模型时,综合模型的R2仅为0.067,纳入后提高到0.246)。
(2)与家人融洽相处的知识和技能缺乏的家庭,夫妻与代际间沟通不畅、互动不良的相对较多,家庭和谐指数会降低。
(3)经济压力对家庭成员承担责任、履行承诺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影响程度有限(其中或多或少有经济压力的家庭约占30%);而工作压力未呈显著性意义主要是因为目前在职人员有工作压力的较为普遍,本研究有56%的家庭中至少一个成员感受到工作压力。同时,由于一些在岗者虽工作压力大,但所从事的职业是自己所喜爱的、能体现个人价值或报酬较高,也未必对家庭生活有负面影响。至于有诸如酗酒、赌博、“啃老”、婚外恋烦恼等等问题也未对家庭关系产生不良后果,主要是因这些问题引发烦恼的家庭并不多(总共为7%,其中为婚外恋等性问题或子女“啃老”所困扰的均不到1%),自述问题严重的更为少见。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被访者会隐瞒属于个人隐私的家庭问题,或问题严重的家庭会拒绝我们的访问。
(4)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不和谐的概率略大些,这或许与年轻夫妇处在角色变换和婚姻调适的磨合期有关,加上年轻人往往自我意识和个性较强,发生冲突后常缺乏妥协的弹性,由此形成不和谐之音;而有70岁以上的老人未必造成赡养负担和压力,主要是因为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家庭的功能各不相同,一些老人虽年愈七十但生活能自理甚至还能为小辈分担家事,或在维护家庭凝聚力方面有促进作用,故该变量未呈统计显著性。
(5)正如大卫?切尼所说,社会资本对于大多数幸福家庭而言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本研究也显示,在有经济、生活或心理困扰时及时得到亲戚、朋友或社区、单位等正式或非正式援助的家庭,通常有更大的概率缓解压力、维持正常的家庭功能。而家庭的经济资源未呈显著性意义,或许与解释变量的选择有关,被访者所首肯的“和一般家庭比较而言,我们家的收入较高”的主观判断仅对“表爱与分享”侧面具有正相关,而未对其他侧面和和谐家庭总指数起作用,主要是该解释变量的效度欠佳,但也可能是经济资源本身与家庭人际关系无相关联系。而家庭藏书量对于家庭和谐度无显著相关(无论使用藏书量的连续变量或是否大于100本的虚拟变量,均未呈统计显著性),则与我们原先的假设所吻合。
(6)在排除了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后,市区的家庭和谐指数仍略高于郊县,尤其在表爱、分享和调适能力侧面,市区家庭显然做得更好些(P均小于.000)。
五、结论、启示和局限
以往的和谐家庭或文明家庭评估体系更多地从社区和行政工作业绩考核为出发点,存在重形式轻内涵、重外在评价轻自我感受以及忽视家庭结构多元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等缺憾。本研究借鉴国外家庭凝聚力、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等度量指标,根据中国的国情建构一个以人为本、定位关系质量的和谐家庭评估体系,并通过上海城乡1200个家庭的经验资料加以量化测试、评估和检验。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将26个具有潜在内部结构的指标有机合成的和谐家庭量表基本符合我们对指标体系框架的预设,该量表分两个层面:家庭凝聚力和家庭适应性,前者涵盖承诺与关爱、表爱与分享两个分量表,后者包含协调适应能力、尊重与包容、内外和谐三个分量表。
统计结果报告,成员间恪守承诺、履行责任、相互体贴的家庭仍占主流,多数家庭在社会经济结构或家庭生命周期发生变化或面临困难、压力时,相互扶持、积极应对的协调适应能力较强,并与邻里、小区和自然和谐相处、相互照应。但在情感表达、营造欢乐氛围以及人际互动中的包容、妥协尚有缺撼。这个结果或许是对一些定性研究学者和大众传媒对当前中国家庭道德滑坡、功能衰退判断的部分纠正。尽管家庭责任淡薄、婚姻伦理失范、孝道衰落等现象确实存在,但未必普遍和严重。同时也提示我们,进一步提升家庭和谐指数需要在人际共处的艺术上下功夫,比如经常用“我爱你”、“亲爱的”等“甜言蜜语”、亲吻、拥抱或意外的惊喜来传情达意;更多地抽时间与家人共渡美好时光,享受轻松和愉悦;对家人的过失和不同意见少一些指责和否定,即使在气头上也不说伤害家人的话、不做伤害家人的事等,使家庭更具亲合力和归属感,日常生活更具新鲜感和温馨感。
对家庭和谐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了文化规范的重要作用,认为婚姻对自己人生非常重要、结了婚就要白头到老的、不赞同现在很少有美满幸福的婚姻和婚姻是爱情坟墓的,认同赡养父母、孝敬公婆是自己应尽义务的被访者,有更大的概率生活在和谐家庭中。而当前影视银屏、小说、杂志、新闻报道中泛滥成灾的婚外情、多角恋以及由此引发的婚姻离散、妻妾争斗、兄弟反目、亲子相戳、尔虞我诈等负面故事、扭曲心理和恶性惨案的过度渲染,严重地夸大了婚姻家庭的黑暗面,加上那些夹杂着抽样偏差、商业利益的所谓咨询公司或网上调查结果的误导,以至傍大款、一夜情、包“二奶”、离婚、家庭暴力、复仇、情杀等被视作触目皆是的普遍现象,不少年轻人甚至不再相信爱情的存在、婚姻的持久,不敢轻易承诺责任、走进婚姻围城。因此,强化婚姻家庭研究,系统、科学地评估中国家庭的实际状况,不给那些非学术、不严肃、哗众取宠的媒体炒作提供大行其道的机会,以及倡导健康、向上、文明的家庭文化,在当前尤为重要。我们也期待受众极广的银屏家庭伦理剧中多一些真情、善良和唯美,少一些滥情、自私和邪恶,以积极向上、和而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信仰引导人们建设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弹性的和谐家庭。
与家人融洽相处的知识和技能缺乏的家庭,和谐指数相对较低的分析结果,显示了普及家庭生活教育和训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婚前教育或家庭生活教育方面所进行的投资和制度推进,以及社会组织、民间力量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为不同需求的家庭提供各种指导和服务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压力对家庭成员履行义务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也给予我们以警示意义。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的背景下,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上采取哪些有效措施,社会政策如何向就业困难家庭倾斜,家庭成员又如何赋予压力以正向定义,将压力视作动力和转机,并涉取家庭内外的支持资源,来减少经济压力对家庭功能发挥和家庭关系的不良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新的课题和挑战。
由于调查成本的限制,本研究仅对其中一位成员进行访问,这必将遗漏或过滤掉一些重要的相关信息,但实际上要收集家中所有成员对家庭关系全面评价的难度非常大,因此,该研究局限也难以避免。后续的研究可进一步在地区比较上作分析,同时设计出效度更高的家庭资源等解释变量。
参考文献
1. 赵士辉、董维玲:《和谐家庭建设读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单艺斌、叶苏平:“关于家庭和谐状况的评价体系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3.“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十一五’测评指标”在上海市民信箱网上可获取,参见http://www.smmail.cn/html/wmjs.doc。
4. 约翰?德弗雷、大卫?H?奥尔森:“美国婚姻和家庭面临的挑战——社会科学家的对策”,《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5. Stinnett, N., & DeFrain, J. (1985). Secrets of strong families. Boston: Little, Brown.
6. 费立鹏、郑延平、邹定辉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参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年版。
7. 刘士勇、宋风英、王龙会、沈鲁平《酒依赖患者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年第2期;张吉营、赵红苏、高静芳:“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年第9期;曾棣、李合群、程子军:“798例大学生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家庭类型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年第4期。
8. Olson, D. H., Gorall, D. & Tiesel, J. (2002). Family inventories package. Minneapolis: Life Innovations.
9. 费立鹏、沈其杰、郑延平、赵靖平、蒋少艾、王立伟、汪向东,“‘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估”《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年第5期。
10. Burr, W.R., Ahern, L. & Knowles, E.M. (1977). An Empirical Test of Rodman’s Theory of Resources in Cultural Contex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9 (3), 505-514.
11. Amato, P. R., Johnson, D. R., Booth, A., & Rogers, S. J. (2003).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arital Quality Between 1980 and 200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5(1), 1-22. Durall, E.M. (1971). Family Development (4th ed.).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Anderson, S. A., Russell, C. S., & Schumm, W. R. (1983). Perceived marital quality and family life-cycle categories: A further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1), 127-139. White, F. A. (2000). Relationship of Family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to adolescent moral though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0(1), 75-91. Foster, M. D. (2000).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s to Personal Discriminution: Does Coping Make a Differenc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0(1), 93-106. Boss, P. (1988). 参见波玲?布思著、周月清等譯:《家庭压力管理》,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Kwon, H-k, Rueter, M. A., Lee, M-S, Koh, S. & Ok, S. W. (2003). Marital Relationships Following the Korean Economic Crisis: Applying the Family Stress Model.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5, 316-325. Warner, R. L., Lee, G. R., & Lee, J. (1986). Social Organization, Spousal Resources, and Marital Power: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1), 121-128. Sanders, J. & Nee, V. (1996).Immigrant Self-Employment: The Family a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231-249.
12. 费立鹏、沈其杰、郑延平、赵靖平、蒋少艾、王立伟、汪向东:“‘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估”,《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年第5期。
13. 资源论代表作有:Burr, W.R., Ahern, L. & Knowles, E.M.. An Empirical Test of Rodman’s Theory of Resources in Cultural Contex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77.39 (3), 505-514.
Amato, P. R., Johnson, D. R., Booth, A., & Rogers, S. J. (2003).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arital Quality Between 1980 and 200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5(1), 1-22. 生命周期代表作有:Durall, E.M. (1971). Family Development (4th ed.).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Anderson, S. A., Russell, C. S., & Schumm, W. R. (1983). Perceived marital quality and family life-cycle categories: A further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1), 127-139. White, F. A. (2000). Relationship of Family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to adolescent moral though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0(1), 75-91. Foster, M. D. (2000).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s to Personal Discriminution: Does Coping Make a Differenc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0(1), 93-106. 家庭压力视角代表作有:Boss, P. (1988). 参见波玲?布思著、周月清等譯:《家庭压力管理》,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Kwon, H-k, Rueter, M. A., Lee, M-S, Koh, S. & Ok, S. W. (2003). Marital Relationships Following the Korean Economic Crisis: Applying the Family Stress Model.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5, 316-325. Warner, R. L., Lee, G. R., & Lee, J. (1986). Social Organization, Spousal Resources, and Marital Power: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1), 121-128. Sanders, J. & Nee, V. (1996).Immigrant Self-Employment: The Family a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231-249.
Burr, W.R., Ahern, L. & Knowles, E.M. (1977). An Empirical Test of Rodman’s Theory of Resources in Cultural Contex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9 (3), 505-514.
Amato, P. R., Johnson, D. R., Booth, A., & Rogers, S. J. (2003).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arital Quality Between 1980 and 200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5(1), 1-22. Durall, E.M. (1971). Family Development (4th ed.).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Anderson, S. A., Russell, C. S., & Schumm, W. R. (1983). Perceived marital quality and family life-cycle categories: A further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1), 127-139. White, F. A. (2000). Relationship of Family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to adolescent moral though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0(1), 75-91. Foster, M. D. (2000).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s to Personal Discriminution: Does Coping Make a Differenc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0(1), 93-106. Boss, P. (1988). 参见波玲?布思著、周月清等译:《家庭压力管理》,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Kwon, H-k, Rueter, M. A., Lee, M-S, Koh, S. & Ok, S. W. (2003). Marital Relationships Following the Korean Economic Crisis: Applying the Family Stress Model.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5, 316-325. Warner, R. L., Lee, G. R., & Lee, J. (1986). Social Organization, Spousal Resources, and Marital Power: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1), 121-128. Sanders, J. & Nee, V. (1996).Immigrant Self-Employment: The Family a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231-249.
14.大卫?切尼著、彭铟旎译:《家庭生活的社会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
(作者:徐安琪,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本研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学特色学科2008年重点项目,原文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